发布时间:2024.06.21 浏览量:1684次
写在前面:合肥一六八中学建校二十余载,培养出一大批国之栋梁,一批又一批优秀毕业生遍布全球各地。他们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在新的学习和工作中大放异彩,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力学笃行,躬身实践。
2020年的高考前一个月,我和同桌“施哥”施奕帆同学一起走在乡村花园的砖路上。当时又结束了一场考试,我感觉良好。在对答案后,施哥没有放过调笑我的机会:“你是想上北大还是上清华啊?”
“别瞎说,不可能的。”我摆了摆手,“我的梦想也就是浙大。我要是能上清华,我请你吃十顿饭。”
两年多后的“五一”节,我在清华大学的紫荆园食堂里开始偿还这十顿饭里的第一顿。施哥依然用他那挑逗的语气,向我保证以后会多来北京蹭我的饭。

坐在食堂里,我的思绪开始回到这一切的开端,我在始信路边一方天地中度过的高中生活。仔细想想,这样预料不到的转折遍布了我的高中三年。在踏入校园的时候,我笃信我会在高二那年考入科大创新班,提前结束高中生涯。然而造化弄人,那年的物理大题我仔细读题三遍,依然弄错了电荷的正负。和同考的人对完答案后,我难以置信,呆坐在操场边的花坛上,无法接受我将必须经历让我无比畏惧的“高三”。当时的我不可能知道,这将是我高中最精彩的一年。
高中前两年,我因为专心竞赛与自招,对课内的知识学习浅尝辄止。我的成绩在年级九十多名游荡,不下不上。我的班主任潘磊老师对此相当烦恼,他认为我的能力不止于此。对当时的我而言,并没有听进这些良言。对于我来说,创新班的马失前蹄是当头棒喝,使我不得不对课内知识认真起来。从创新班失利到零模之间的半个月时间,我第一次拿起习题册开始刷题。对于零模,我的想法是能提升多少提升多少吧。抱着这种心态,我走进了潘老师办公室询问成绩,看到的是他复杂的表情。“年级第13名。”他在沉默后,轻描淡写地说道。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他表情的意义:既有一种“我早就知道”的得意,也有一种“你早干嘛去了”的嗔怪。这是我高三生涯的开局。

高三上学期,我的成绩继续在十来名上下移动。有一次吉星高照,获得了年级第四。然而这个成绩对于有一个人而言是不满意的,那就是语文孙华老师。“你语文扣的分比其他课加起来还多。”当我找孙老师炫耀成绩时,她被我小人得志的模样气笑了。孙老师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在遇见孙老师之前,我满分150的的语文最低考过90分。遇见孙老师后,语文课后的课间便充斥着我们针对各种题目的辩论。“你的语文积累是非常足够的,缺的就是做题方法。没关系,我能教会你。”这是孙老师对我的定义。高三一年,我的语文没有下过110分。虽然很多时候因为我解题“钻牛角尖”的坏习惯,语文成绩依然不尽人意,但孙老师对我的影响却超越了成绩本身。她是我高三生活中一位闪光的朋友,我可以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她办公室,她依然会腾出时间和我闲聊。或许为师者的真谛正是这种陪伴吧。
高三下是一段紧张但又平淡的时节。正因如此,一些片段在我的记忆中显得尤其突出。生物杨贤云老师每次对选择题答案前都说:“我们来盖棺定论啊。”于是每次考试后他进入教室,全班都会此起彼伏地大喊:“盖棺!盖棺!”数学祝文革老师在某次讲概率题时发现大家注意力涣散,于是话锋一转,饶有趣味地向大家回忆起三十年前百货大楼的一次抽奖欺诈事件。物理李孔望老师在读题之后,都会把手指攒在一起在空中虚空一点:“说明啊!”英语陆广武老师更是有无数关于他年轻时一表人才的传说在班里口口相传,被大家称为”吴彦祖”。在这些片段中,穿插的是一次次的考试,高考一天天的倒计时。平淡如水的日子一直流淌到高考后,流淌到我的强基计划招生考试,流淌到我进入清华大学校门的那天。
如今的我在清华大学未央书院就读数理基础科学和机械工程双学位,一转眼也来到了毕业的边缘。我在大学做过社工,进过校团委,当过社团骨干。如果细细展开,这四年如过去三年一样峰回路转。但高中三年还是在我的记忆殿堂中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就像孩提时看到的某个电视节目,一生都不会淡忘其中的细节。思来想去,或许精彩的并不是这些转折本身,而是一路与我同行的人。归根到底,我记住的是老师们铿锵的声音,是朋友们鲜活的面孔,是一同经历的教诲和成长。始信路和澜飞湖之间的不只是一群建筑,更是一个舞台,我在舞台上和许多人一起出演了我人生最富有活力的三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陪伴,或许我在某一个转角就会陷入绝望,失去前行的动力。而正是因为他们的陪跑,我才能相信峰回路转,永远昂首向前。
(供稿:杨朔宁 马奕芹 审稿:任杰)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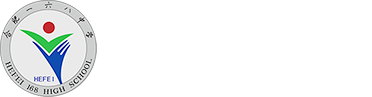
 0551-63803900/63803905
0551-63803900/63803905
咨询热线
集团学校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