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稿:高静怡、吴丹丹 审稿:张文生 发布时间:2025.03.22 浏览量:131次
晨雾漫过寿春城堞,楚风掠过瓮城箭孔。青铜编钟的余韵在墙砖苔藓间蛰伏千年,待少年足音叩响云雷纹的哑谜,将《楚辞》残章织入护城河的粼波。
车辙映入盟书帛
暮春淮风掀起窗帘,恰见楚灵王伐徐的车辙遗留在柏油路下。临涣渡口摆渡人摇橹的弧度,与孙叔敖治芍陂的夯歌莫名相契,波纹间浮沉着陈轸说楚的机锋。指腹温热处,恍若触到春申君递过合纵竹简的指尖。

导游振袖如公孙龙开卷,指城堞讲述项橐孔旧事。但见朝霞化作诸子帛书,将两千载机锋都付与少年辩声。
淮水已在我们身后绾起粼粼诗结。忽悟这条曾载过楚辞汉赋的河流,原是将千载文脉化作了流动的韵脚,而我们的车轮正碾过某位古人遗落的平仄。
郢爰烙进少年瞳
推开朱漆馆门时,檐角铎铃忽作楚宫徵音。导游擎起仿制错金节,光斑游走处,春申君调兵符在展柜玻璃上洇出虎形暗纹。
“此非器皿,乃楚魂所寄。”导游叩击云纹漆耳杯,杯中涟漪漫过《招魂》残卷。
最摄魂当属蔡侯青铜剑展区。导游以伞柄比划季梁谏攻随的轨迹,刃光劈开的光隙里,但见随侯珠化作穹顶射灯,将我们身影投作列国纷争的皮影。五十二双睫毛在青铜器前织成细密的帘。导游解说蔡侯钟铭的尾音未散,后排已绽开春蚕食叶般的笔记声,笔尖沙沙似在复刻范铸法的千年沉吟。

转过屈子涉江浮雕,导游忽掀开素绢:“诸君且看,此非帛画,实为楚巫招魂幡残片。”众人屏息间,玻璃幕墙外八公山云气涌入,将我们足印烙成郢都旧巷的陶砖纹。有稚子指认玉璧中血沁,说是卞和泪痕未干,却见那抹殷红原是晚霞漫过淮南王丹炉的残照。
二十余部手机屏亮起星子,摄像头聚焦时自动消音的默契里,连尘絮都悬停在射灯光柱中礼敬。
晨阳漫过楚式连廊时,青铜神树正将斜阳锻造成六十四枚金叶,檐牙间栖着的朱雀昨夜尚在《天问》篇中振翅。竹牍裂痕间浮出少年们来时的车辙——原来两千载光阴,不过是楚帛画未干透的墨渍。
城砖烙着秦邮戳
寿县古城墙叠压着七朝夯土。北宋青砖上留着抓钉锈斑,像嵌在砖里的黑曜石;明代补砌的墙段里,糯米灰浆仍泛着琥珀光泽。瓮城马道石板上,深浅不一的凹痕藏着元人铁蹄与民国黄包车的辙印。

水门闸槽内壁布满凿痕,南宋守军磨剑的砺石与清人修闸的钎印在此重叠。东门敌台拐角处,半块万历年间铭文砖探出墙面,字缝里寄生着二十一世纪的爬山虎。
最奇的是北城墙断面,剖面分层清晰如史书——战国版筑土芯裹着唐夯层,外层宋砖夹缝中,竟生出几株元代《农书》记载的救荒野菜。护城河对岸现代楼宇的玻璃幕墙,此刻正将古城轮廓折映成北宋《千里江山图》里的青绿笔触。
豆乳洇湿丹砂卷
八公山豆腐坊的石磨卧在霞光里,檀木手柄泛着包浆。老师叩击磨盘:“淮南王在此丢了颗豆子,两千年后长成这山麓的月华。”泡发的黄豆从指缝滑落,像一斛斛未雕的羊脂玉坠入青石齿槽。
推磨声惊醒了檐角风铃。同学们轮流转动木柄,碾缝间淌出的浆汁在陶盆里织出素绡。


最妙的是磨芯发热时,水汽裹着豆香漫过窗棂。某个埋头推磨的剪影突然定格,原来他发现木柄上叠着无数代掌纹,最新鲜的指纹正与他的汗水交融。山风携着淮南王衣冠冢前的柏子,将《招隐士》的辞章烙进豆香。
归途山径上,豆香仍在指缝酿着未央的月光。归途车灯刺破薄雾,恍若昔年楚人秉烛夜游的光轨——原来历史从未退场,只是借霓虹在柏油路上重书凤鸟图腾。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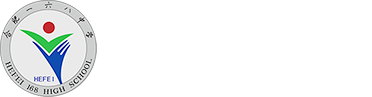
 0551-63803900/63803905
0551-63803900/63803905
咨询热线
集团学校地址